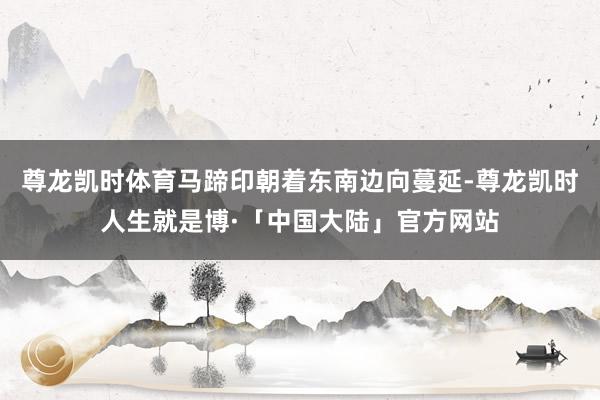

1937年3月,红三十军二六五团的战士们瑟索在祁连山背风的山坳里,棉军服早已看不出底本的热情,血渍混着雪水冻结成硬壳,贴在身上像层冰甲。“盘点东说念主数!”团长邹丰明的声息被风吹得七零八落。通讯员数了三遍,临了蹲在雪地上,用冻裂的手指在雪地里划:“团长,能站着的,不到五十个了。”邹丰明望着山坳外,昨夜的激战留住了成片的尸体,有赤军战士的,也有马家军马队的,马尸的肚子被剖开,内脏冻成了紫玄色,那是饥饿到顶点的战士们独一的“食品”。更远方,马家军的马蹄声像闷雷滚过雪原。三面包围的马队正在减弱包围圈,后堂堂的马刀在雪光反射下,刺得东说念主睁不开眼。引导所的破旧帐篷里,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成员们围着一盏油灯,灯炷爆出的火星子落在陈昌浩的破棉裤上,他浑然不觉。“同道们,情况等于这么。”陈昌浩的嗓子哑得像被砂纸磨过,他刚从前沿阵脚撤下来,左臂缠着渗入血的布条,“马家军三个旅把石窝山围死了,咱们只剩不到三千东说念主,弹药不及三成。”帐篷里的冷气仿佛更重了,有东说念主下意志地裹紧了衣着,油灯的光晕在每个东说念主脸上投下深深的暗影。“我和徐上前同道,决定离队东返。”陈昌浩的声息蓦然低了下去,“回陕北,向中央弘扬西路军的情况。”帐篷里已而死寂。王树声猛地抓紧了拳头,指流弊“咔哒”作响,这位红九军军长的警卫员昨天刚糟跶在他眼前,胸口插着一支马枪。李先念靠着帐篷壁,军帽压得很低,没东说念主看清他的热情,只看到他放在膝头的手,逐步捏紧了那把追随他多年的驳壳枪。“咫尺,建造西路军责任委员会。”陈昌浩顿了顿,眼神扫过世东说念主,“由李先念同道斡旋讲求军事引导,教导军队不竭作为。”李先念猛地昂首,军帽下的眼睛亮得惊东说念主。他刚在前沿搏杀了一整天尊龙凯时体育,脸上还沾着干涸的血渍,颧骨上一齐被马刀划开的伤口结了黑痂。“我效用呼吁。”他的声息不高,却像钉在雪地里的木桩,稳得很。散会时,李先念叫住了正要走出帐篷的通讯员小张。这孩子才十六岁,是从四川随着赤军出来的,冻得嘴唇发紫,正往怀里揣一块冻硬的青稞饼。李先念解开我方的粮袋,倒出半块饼塞给他:“拿着。记住,多带出一个战士,等于给翻新多留一颗火种。”寒风从帐篷破绽钻进来,吹得灯焰直晃,他的影子投在帐篷壁上,像石窝山岩壁上那株被风雪压弯却不愿撅断的青松。天没亮时,军队启动更正。雪没到膝盖,每走一步皆要费尽全力,棉鞋里的雪化成水,又冻成冰,踩在地上“咯吱”作响。李先念带着照看们在前边探路,他的绑腿磨破了,泄露的脚踝冻得通红,却走得比谁皆快。在一个背风的山坳里,责任委员会再次碰面。李先念蹲在雪地上,捡起一根冻硬的树枝,在雪地里划出石窝山的地形:“马家军主力在东、北、南三面,马队纯真性强,咱们硬拼详情不可。”他的树枝指向西侧,“唯有这里,雪线以上,他们的马队上不去。”“西进?”王树声猛地站起来,步枪顿在雪地上,溅起一派雪沫,“那是末路!祁连山土产货连牧民皆不去,咱们进去等于等死!”他的声息带着哭腔,“往东走,围聚陕北,还有可能找到主力!”李先念昂首看他,这位老战友的眼眶通红,王树声的警卫员昨天为了掩护他,被马匪的长矛刺穿了胸膛。“树声,”李先念的声息很千里,“东边有马家军两个旅,咱们这点东说念主冲出去,能活几个?”他指着雪地上的道路,“西进,钻进雪山深处,等他们疏忽了,再找契机往新疆走。哪里有苏联的救援,咱们能活下去。”王树声还思说什么,却被李先念按住了肩膀。“我知说念你思回陕北。”李先念的手很烫,“但咱们咫尺不是为我方活,是为西路军剩下的弟兄活。”天色微明时,队列分红了两路。王树声教导右支队,马蹄印朝着东南边向蔓延,很快灭亡在风雪里;李先念的左支队则踩着没膝的积雪,一步步向西挪。两说念辙印在雪地上并行片刻,就被呼啸的风雪抹平,仿佛从未存在过。西进的路比思象中更难。第三天清早,一个叫赵拴柱的河南兵蓦然瘫坐在雪地上,放声大哭:“我不走了!这破方位,走出去亦然死!不如且归跟马匪拼了!”他的话像块石头扔进水里,几个年青战士也随着停驻脚步,眼里尽是幽闲。李先念让队列停驻来,他蹲在赵拴柱身边,解开我方的粮袋,内部只剩一把炒面。“拴柱,”他把炒面分了一半给年青东说念主,“我知说念你思家。我也思,思湖北黄安的热炕头,思我娘作念的红薯粥。”他指着远方的雪山,“但咱们得谢世出去。谢世,能力回家;谢世,能力给糟跶的弟兄报仇。”赵拴柱抹了把脸,雪水混着泪水往下淌:“李司令,我不是怕死……等于以为,看不到头。”“有头。”李先念站起身,从背包里掏出一面卷着的红旗,抖落上头的雪,“随着它走,就有头。”红旗是用伤员的血染的,边角照旧磨破,但那抹红在白雪衬托下,相配夺目。有七个战士如故决定离开,他们说要往东打游击。李先念没拦着,派了一个排护送。“若是能活下来,记取往新疆走。”他给他们塞了临了小数弹药。那支队列走出不到三里地,就传来了密集的枪声,断断续续响了半个时刻。自后,唯有两个断臂的战士爬回营地,他们说,刚翻过一个山梁就撞见了马家军的马队,排长呼吁着“你们快跑”,带着东说念主冲了上去。赵拴柱抱着那两个伤员,哭得满身发抖。李先念站在雪地里,望着枪声传来的标的,久久没动。风把他的头发吹得乱蓬蓬的,没东说念主知说念他在思什么,只看到他回身时,眼眶红得锐利。夜里的温度降到零下三十度,战士们彼此抱着取暖。李先念把那部手摇电台裹在我方的棉大衣里,发报员小郑的手冻得像胡萝卜,连电键皆按不动。“司令,电板快没电了。”小郑的声息带着哭腔,“发不出去了。”“再试试。”李先念把我方的手套摘下来给他,“给延安发,说咱们还在,问他们咱们该往哪走。”小郑咬着牙,用冻僵的手指按动电键。“嘀……嘀嘀……”耳机里唯有噪音。他正要澌灭,蓦然,一阵微弱的“嘀嗒”声钻了进来。“有了!有来电了!”小郑的声息发颤,手指速即地纪录着。李先念凑以前,看着电文纸上的字:“向新疆更正,中央会设法策应。”他把电文纸紧紧插在雪地上,用劲拍了拍小郑的肩,声息里带着从未有过的焕发:“听见了吗?党中央在等着咱们!”战士们围过来,看着那张薄薄的纸,有东说念主哭了,有东说念主笑了。赵拴柱蓦然站起来,朝着延安的标的敬了个礼:“党中央没忘了咱们!”接下来的路,像是在刀尖上走。翻越雪线时,不少东说念主膂力不支,走着走着就倒在雪地里,再也没起来。李先念让群众彼此搀扶,年青的帮着大哥的,没受伤的背着伤员。有个叫马三喜的炊事员,背着一口铁锅走了七天,铁锅上的补丁比锅底还多。有东说念主让他扔了,他说:“等出了山,我给群众熬肉汤喝。”走到第二十天,马三喜倒下了。他怀里还揣着半块锅巴,是他省了三天的口粮。李先念把锅巴分给了几个伤员,我方提起那口铁锅,不竭往前走。“三喜说了,要熬肉汤。”他对身边的战士说,“咱们得带着锅出去,替他熬。”第四十三天清早,当第一缕阳光照在星星峡的山口时,哨兵蓦然喊起来:“有东说念主!是穿军装的!”李先念举起千里镜,看到远方走来一队东说念主,举着红旗。他笑了,笑着笑着就哭了,那是党中央派来策应的队列。队列走进星星峡时,只剩下四百多东说念主。每个东说念主皆瘦得脱了形,棉衣褴褛不胜,脚上的鞋早就磨没了,光着脚踩在沙砾上,留住一串串带血的脚印。但他们手里,还紧紧攥着那面染血的红旗。自后,这些从雪山里走出来的战士,成了翻新的火种。他们有的去了延安,有的留在新疆学习军事本领,还有的随着李先念回到了华夏战场。马三喜的那口铁锅,被带到了延安,炊事员们用它熬了整整一锅肉汤,祭奠那些没能走出雪山的弟兄。1949年,当李先念率领军队自如湖北时,际遇了赵拴柱,他已是别称团长,胸前挂着满满的勋章。“司令,”赵拴柱指着死后的队列,“当年您说的火种,咫尺成燎原之势了。”李先念望着远方的大别山,思起了祁连山的雪。那些在风雪中倒下的战士,那些冻僵在雪地里的年青样子,那些在帐篷里油灯下的不眠之夜,蓦然显明起来。他知说念,石窝山的抉择莫得错。的确的火种,从来不是某个东说念主,而是在绝境中不愿灭火的信念。